出路
本周在尝试摆脱掉颓废的状态,开始焦虑出路,也到了要焦虑出路的时候,又到了’好像其他人都有了清晰的目标’的时候,高考之前是这样,现在又进入了这样的情景,不过大部分人应该都是迷茫的,然后都会去看其他人,他人好像都是有方向的,保研的保研,考研的在准备考研,工作在准备找工作,看别人之后,再看看自己是迷茫的,然后就焦虑起来了。

对我来说,之前一直想的是去工作,但是24年一整年我都没有真正在为这个目标做什么准备,混了大半年之后,意识到我并不热爱计算机,并不热爱安全,我对计算机/安全感兴趣这个故事已经讲不下去了。
热爱需要的是擅长某件事情并且自己能够确认自己擅长这件事情,前者需要刻意练习,离开外围,深入到事情的内核之中,这点我做的不够,浪费了很多时间在外围,后者需要我主动或者自然的从外界获得的反馈中培养一种确认感—我能够做好这方面的事情,后者比前者更重要,而在这方面我是匮乏的,我并不擅长这么做,在这之后,我才意识到我这方面能力的匮乏,我缺乏这种从外界反馈中肯定自我的习惯,就连高考,这件我目前来看做的还行的事情,我都没有什么胜任感,我只是莫名奇妙的就这样了。
当然找工作并不需要什么热爱,热爱是要在生存之上的,而我还没有处理好我的生存焦虑,我并没有谁能为我兜底,没有工作,我会直接掉到地上,成为最底层。虽然成为三和大神并没什么不好,成为流浪汉也并没有什么不好(有一种"如果有一天我能割舍掉一切,去流浪,去朝圣,就算死在路上,我的人生也圆满了"的意味,倾向),但是我并不能丢弃掉“让父母安度晚年”这一世俗欲望。
高中的时候,我在日记中将朋友这一关系想象成丝线(心盲症者的抽象想象),与人交互是在增长这一丝线,而将与亲人的关系想象成锁链,很难割开,但是也只不过需要付出的代价更多而已,但是我后面意识到了,很大程度上,我愿意带着这一锁链继续跳舞,我还是想要去实现这一欲望。我还是需要通过正常的方式去解决我的生存问题。
那就找工作吧,学测试,刷力扣,背一下八股文,匆匆忙忙的准备一下面试吧。但是我又对这些有一种无力感。主要的无力感来源还是面试。我缺乏很多社会化需要的技能,我极度社恐,INTP这个符号里面也许只有I是确认无疑的(我记得是92%这个数字🥺,去翻了一下,一年多之前的图居然还在)。我不会表达,不怎么能将一些东西解释清楚,这点一方面可以溯源到高一,疫情半年在家,我每天基本上都没有说话,后面也就忘记说话了(身体和思维),加上回到学校之后把注意力放到了应试里面,后面我也就不怎么会表达了,另一方面溯源到家庭教育吧,这方面我是缺失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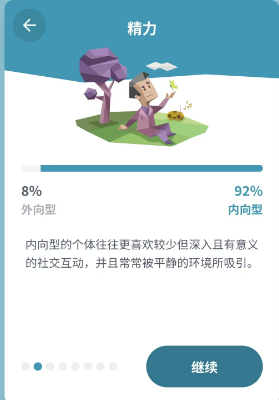
相较于工作,我并不怎么愿意继续呆在学校这一环境(甚至于现在就想逃离),我已经待在学校够长了,我渴望早一点进入下一阶段,不管是以怎样的方式进入吧。而选择读研的话,就又得压抑几年了,而且也只是把现在的焦虑推迟了一些。不过读研对我来说并非全是坏处吧,可以让我多一些时间,再多一些社会化,多去主动培养一些自信。
那考公呢,国考,省考,国企事业编,我确实更倾向稳定和低强度这两个属性,但是我还是要解决我的无力感。
除了这几项呢,读研,工作,考公还有什么?我为什么会出现摆脱这几种出路的想法呢,主要是因为焦虑的太过了,以至于让我又想要重开了,现在让我回忆回忆当时的感受,我也说不太清楚,看见绳子,看见衣架,看见插孔,我就马上联想到重开的方式,也去淘宝看了一下亚硝酸钠,50块钱,好像比农药更舒服。(这估计就是我进入这种模式的诱因之一,这周在X上看见了两三个吃亚硝酸钠的贴子了)。
可惜我就是想的太多了,没能行动,最后也只是跟朋友发了一句“心跳声好吵”,然后凭据我的深厚底蕴,喊出来了上帝,喊出来了佛法。或许面对出路这件事情,我也只能喊出逃避这一手段了(虽然我在认识上知道并没有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事情,或者说任何事情都是对的。活着是在逃避死亡,自杀是在逃避活着,并没有哪一种更加正确,但是我更多的还是生活在常识的世界里面,常识的世界里面充满二元对立,一侧是阳,是好的,是正确的,而另一侧是不好的,不正确的),也许我可以直接辍学,流浪,服务员,出家,网管,扫大街,或者在哪个过程中死掉,也许我可以混完毕业证,去当客服,进电子厂,去干铁人三项,去走线,也许我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培养我自己,然后才能进入轨道。
残缺与上帝爱我
我陆陆续续觉察到了这些我无法改变的事情,我深感无力,我永远都无法改变我的这些残缺(或者叫做残疾,特质,多样性),身体层面上的矮个子,文化层面的家庭教育的缺失,大脑层面的多感官心盲症。
矮是我觉察到的第一个我无法改变的事情,经历了这么多年,从高中深刻的感受到矮带给我的痛苦开始,采取了一些对治的手段,高中时逃向应试教育,进入大学之后逃向学习技术,不再像最初感受到这点时那样痛苦了,对此的信念已经达到某种平衡了,痛苦被消解掉了一部分,但是让我去回想那些情景,仍然会感到痛苦和无力,使用同理心之后,我能够理解其他人的行为,这是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嘲弄,我们在日常中是习惯去嘲笑倒霉蛋的,我只是恰好在这件事情上成了倒霉蛋,但是这种认识层面的理解并没有改变我的感受,只是一种转移注意的手段。
身体层面的残缺在高中或者在高中之前就感受到了,而文化观念上的残缺是上了大学之后才慢慢觉察到,离开了中学的苦闷环境,我有了一些心力来看世界,看周围的人,看的结果就是我意识到了“相较于更多存在于想象中的物质层面的匮乏,家庭(用流行的词来说,叫原生家庭)给我带来的文化,观念上的匮乏更加严重”,我后面与世界相处的方式都有这些来自家庭的原型的参与,我与其他人的相处方式来自我与亲人相处的原型。
一个观念生长只能生长在一堆观念之上,那些处于我信念系统底层的塑造我三观的观念,那些我应该在生命早期中接受到的观念是缺位的,也不能说是缺位,是有一个信念系统被建立起来了,只是比较破烂,不能很好的支撑我而已。底层的观念是匮乏的,进而在观念之上的应用层面的各种能力也是匮乏的(可以叫做’软实力’)。可以说,我只经历了学校的教育,而CN的学校教育早已崩溃,十八岁之前,我也没法逃离,直到进入大学,才有了一些空间,一些进行自我教育的空间。

我看世界的方式本身居然也是残缺的。心盲症,可以算得上是脑残了,脑部功能残缺的简称而已。在我接触到国内心盲症群体之后,才从其中的一些人口中了解到脑残这个词的本来意思。怎么算不上是脑残呢,比正常人少了很多功能呢,2%的比例,对我来说,还是更加稀有的多感官心盲症,也许只有0.5%?这种看世界的方式的残缺,可以看成神经多样性吧,但是站在世俗世界的二元对立角度下,或者说站在’正常人’的视角下,这就是残缺。这一残缺对我的影响更加重大,文化,观念算是在应用层了,而心盲症是发生硬件层或者说是操作系统层的问题,我‘看世界’的方式本身就是残缺的,是匮乏的,并且永远会是这样。
我大脑中没有声音(心音)。音乐从来都没有进入我的世界,我直到高中才意识到身边的人,大多都有听音乐的需求,都能享受音乐带来的乐趣,而我只能通过歌词来理解音乐,无法在脑海中“听到”旋律。我脑海中也没有味道,吃饭更多像是生理需求,而不是享受过程的乐趣。除了视觉、听觉和味觉的内在体验缺失,我还没有完全感受到其他的一些感官的缺失对我产生的影响。已经意识到的缺失,总能有办法去代偿,通过关注歌词来理解音乐,理解其中的情感,通过正念来从吃饭中获得美好体验。而那些我还没有意识到的缺失,却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我。
高中读过《被讨厌的勇气》,除了课题分离,目的论这几个概念之外,印象深的就是里面提到的宁静祷文。⌈亲爱的上帝,请赐给我平静去接受不可改变的事,赐给我勇气去改变应该改变的事,并赐给我智慧去分辨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当时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只是感受到了身体层面的不可改变的带来的痛苦,尝试平静的去接受,虽然到如今仍然难以平静,更多的是采取了逃避手段,觉察到的不可改变越多,就越发的想要逃避,以至于逃无可逃,只能逃到死亡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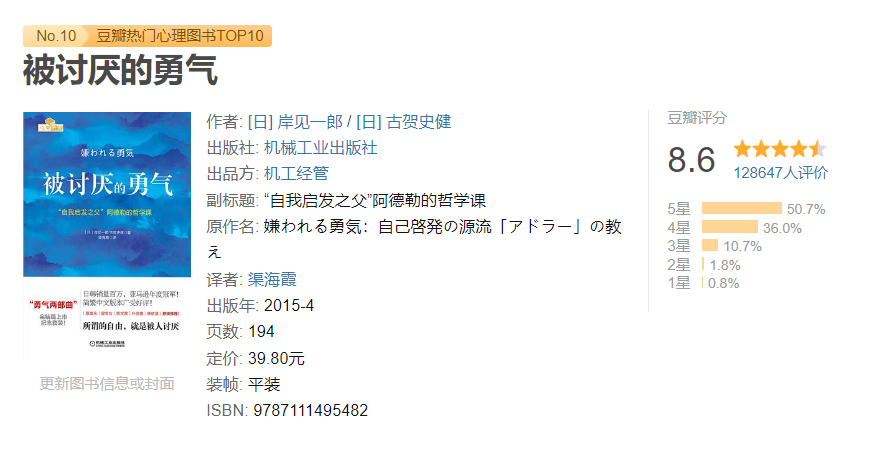
不过还好,死神给我推荐了宗教,依靠宗教这一究极手段,依靠信仰这一非理性方式,大概率能够让我拥有一些平静(理性在意识,生命的领域必须得承认自己是有限的,理性只是生命的一种手段,用语言和思维这些理性的手段捕捉不到所谓的’生命的意义’,语言,思维相较于感受要更加抽象,也就意味着更加失真,‘感受’要比语言和思维更加真实)。可惜我并不能很好的接受’功德’,‘轮回’,‘戒律’这些古老的设定,也许去天堂还是地狱得看你这一生吃的橘子数量🍊,‘上帝’也一直在进步呢🙏
也许如史铁生在《好运设计》里面说的吧,上帝爱我,通过这些巧妙的设计,想让我意识到目的的绝望与虚无,让我有足够的痛苦不得不将目光从结果转向过程,这是对付绝境的唯一手段。‘一个只想(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剥夺的,死神也无法将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不精彩的过程…相反坏运更利于你去创造精彩的过程。于是绝境溃败了,它必然溃败。你立于目的的绝境却实现着、欣赏着、饱尝着过程的精彩,你便把绝境送上了绝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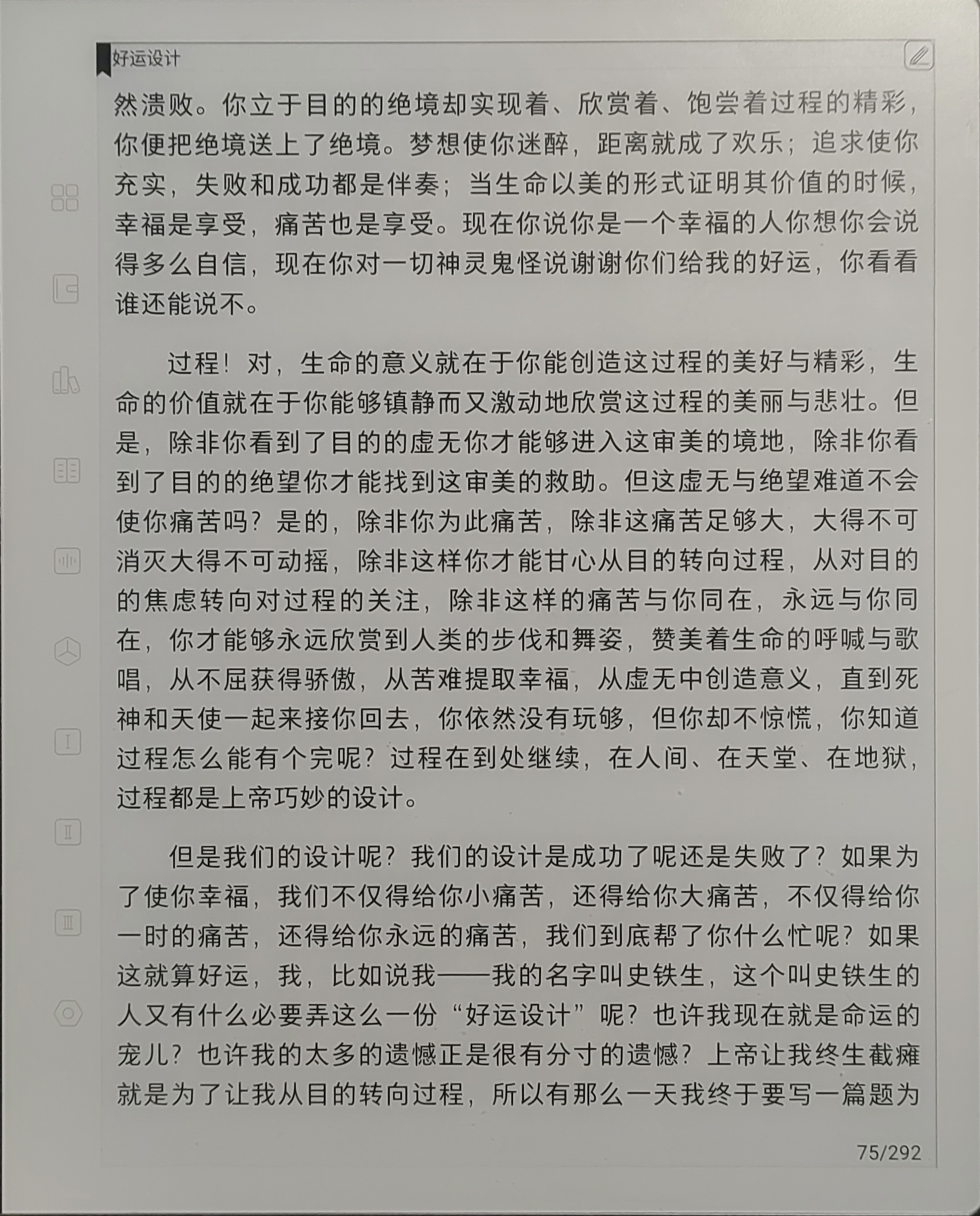
本周在读
本周最开始按着之前的想法,看了一些思想实验,找了一本《直觉泵与其他思考工具》,但是并没有看多少,看不下去的书,我就直接放弃掉,书是读不完的,而有一些书是绕不开的,我没有在对的时间遇到这本书,看不下去了,就先不看了,如果是这本书是经典,之后我大概率还是会从某个地方遇见的。
之后看了一些《与神对话》,这本书也是很早就遇见过了,好像是大一时就遇见过,但是当时并没有在灵性,精神的领域有什么需求,看见这个书名,就直接被劝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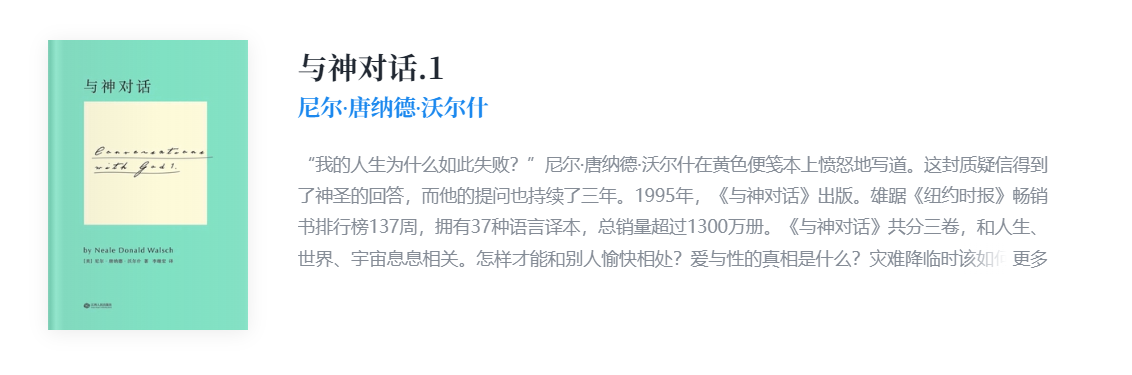
这本书并不是什么基督教的经书,来源于上世纪西方的新纪元运动,书名的神,并不是一般意义上“上帝”,而是一种泛神论,万物一体,这个整体就是神。也并不是一本所谓的洗脑的书籍,确实向我展现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一切都只是视角),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是自洽的,也许不需要用自洽这个词,毕竟这是信仰的领域,信仰领域的知识与科学领域的知识的定义并不相同(在神学的领域,谁谁谁死之后复活是知识,而在科学的领域,知识是需要具有普遍性)。

信仰并不意味着反对科学。我理解的信仰(宗教)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目前就是由科学(理性)塑造而成,怎么可能去反对我生活的这个世界呢,但是生活的全部,生命的全部并不只有理性,科学是理性的视角,但是并不是什么生活的规则,并不是什么生命要遵守的戒律。
回到这本书吧,我其实还没看多少,5%不到,但是看这本书需要的心境已经消失了一些,这本书和《当下的力量》一样,更多的是需要感受。我估计会尽可能的让自己处于那种在感受的心境,尽可能的去看一些,看不下去了,就换其他书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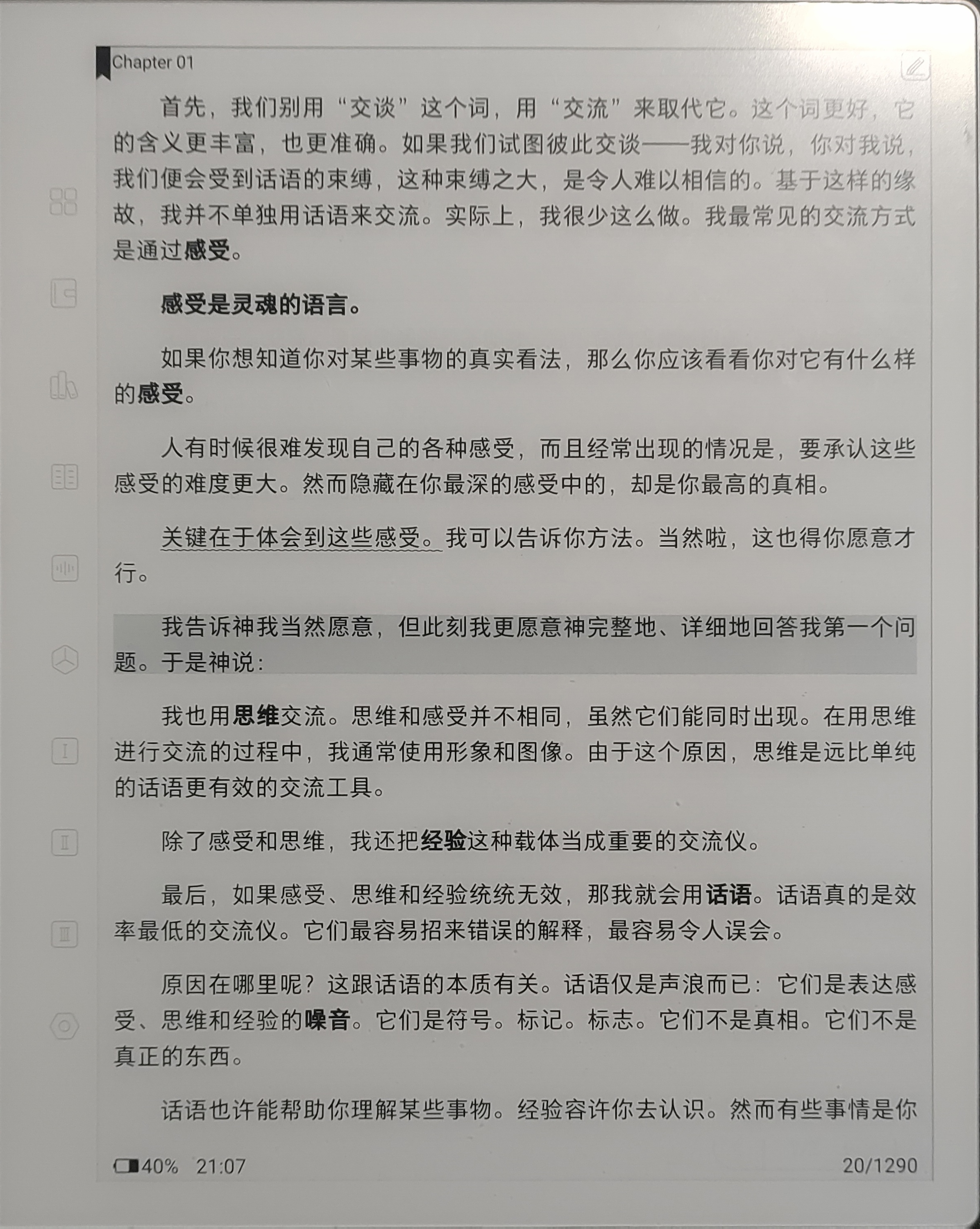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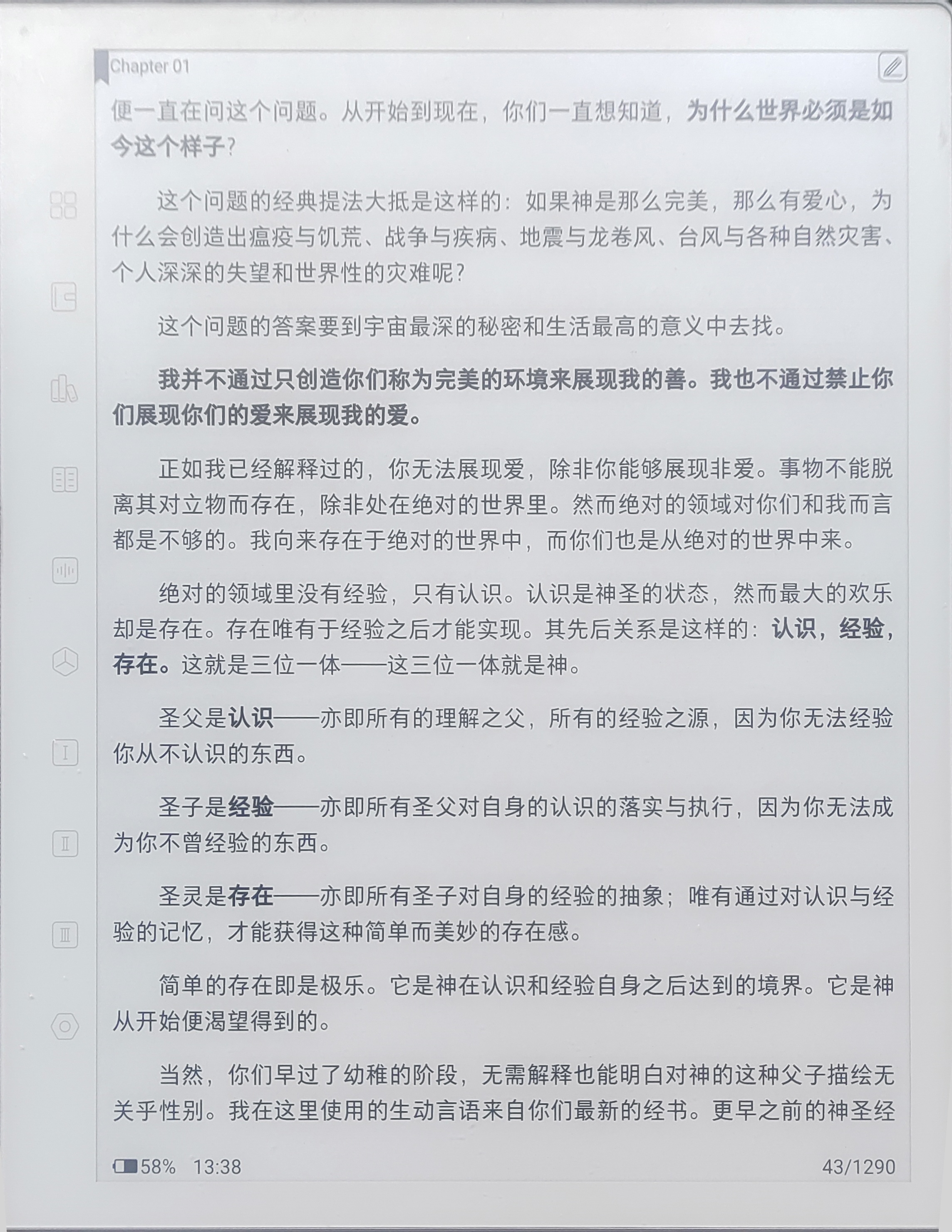
l1uyun
胡言乱语,就先说这些吧。下周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