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篇有些长的记录。
召唤
“饿了应该吃饭吗?”
这个显得有些荒谬和愚蠢的问题,是我暑假回家后,在脑海中产生的疑问。
起因是我在学校往往只吃两餐,但是回家后,家里的作息是每天吃三餐,于是我被要求“应该”吃三餐。
在学校时,我并非因为睡过头而跳过早餐,只是不想吃,甚至有些享受饥饿感。我为我的“不想吃”找到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标签,叫做轻断食。将一天的吃饭时间控制在八小时内,剩下的十六小时不摄入任何食物,从而让身体进入燃脂模式。这能够增强免疫系统的自噬反应,这在我脑海中是现代版本的辟谷。
回家后,我的习性与家庭作息之间始终存在不匹配,我和家人解释了我想要挨饿的想法,他们不能理解只能接受我的做法。这种接受在我脑海中仍然激发了一些报错信息,于是那个在家永远会是(退行回)孩童的我,在脑海中发出了开头那个愚蠢的问题。
跨越门槛
饿了应该吃饭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切入点在“应该”,这句话是一个价值判断,而饿了是一个事实。
我们能够在不同层级观察到“饿了”这一事实——主观上感受到饥饿感,外在表现出萎靡不振、肠胃蠕动发出声响、仪器上显示血糖水平下降、脑中出现饥饿对应的特定神经元放电模式。但是休谟告诉过我们,从事实出发无法推断出价值,只有从价值出发才能得到价值。张三杀了人,仅仅从这一事实出发,我们无法得到“张三应该受到惩罚”,只有在“杀人者应该被惩罚”的价值前提下,才能推断出“张三应该受到惩罚。”
“饿了要吃饭”这一规范性命题背后,也隐藏着一些我们未曾意识到的价值前提,例如“饥饿是痛苦的”、“减少痛苦是好的”、“我们应该避免痛苦”。追问这一价值判断抵达的终点是——生命是宝贵的,我们应该维持我们的生命。
但是这个价值判断来自哪里呢?我们凭借什么得出了“生命是宝贵的、我们应该维持生命”这一价值呢?
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们为什么要迷信生命的价值呢?(是的,一个无神论者并不只是意味着对自然规律祛魅,而是意味着不再神化一切——宇宙、国家、传统、文化、理想、希望、意义、人生、生命……)
鲸鱼之腹
由于在最近一年内,我有过怀疑和否定这一终极价值的体验,在这些经历中,我逐渐发展出一种狡猾技巧。使用这一技巧,我不再持续怀疑或否定生命价值,我也不必回到默认这一价值的状态。
我不必停止追问,而是可以使用我从现象学那里学到的方法,我可以对这个东西加上括号。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暂时对此保持中立,悬置判断。然后呢?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在我这样做之后,我马上就意识到了这是一种观察者视角,并且与我对佛法、灵性的探索联系了起来。
我饿了,我痛苦了,我应该吃饭,这里的我是什么?我是生命的主体吗?我是一个行动者吗?吃饭或者说维持生命这个动作是我主动在进行吗?也许我只是一个观察者,饿发生了,然后吃饭发生了,而我只是在旁边看着这个自动化过程发生,这个过程不需要一个“我”。
这是我熟悉的视角——我很痛苦,我很焦虑,但是没事,痛苦是无常的,是幻觉,焦虑也是幻觉,我也是幻觉。 自我是色受想行识这五种东西和合而成的,而这五种元素是无常的(佛法视角);自我只是一个符号,是一个故事,当下我向未来我谈论过去我,自我产生于三边对话之间,当下的我只是一个占位符,而并非有一个稳定不变的本质(符号学视角);自我只是大脑涌现出来,用于更好预测外部变化,节约生物体能量,提高生存概率的机制。当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退去,自我也就消失了。(神经科学视角)
我让gemini基于观察者视角生成了一幕情景剧,作为哲人的我得出这是终极的虚无、疏离,作为行者的我得出这是终极的平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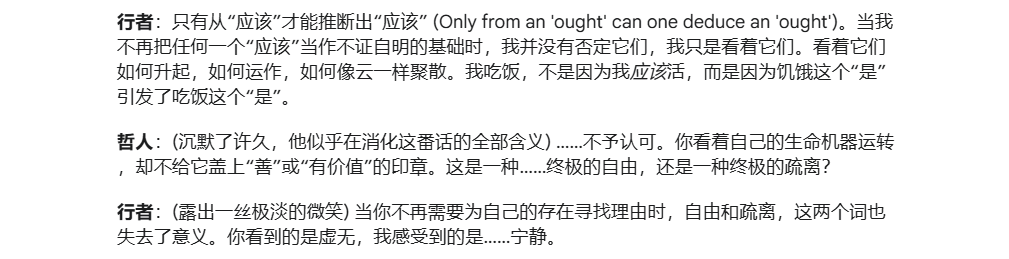
第一次探索就只到了这里,在这个视角里面,我解决了我遇到的问题。我没有必要肯定终极价值,没有必要否定终极价值,我也没有必要肯定我。自我只是一个幻觉,那就保持观察者状态持续觉察这些幻觉吧。
我过去一直相信这一视角,这种状态也许叫开悟、超脱或是证果?这一状态意味着,人生从第一人称游戏切换成了第三人称游戏,从csgo切换成了吃鸡。切换之后,属性不会变,装备也不会变,环境也不会变化,但是游戏变了。
深渊
我对青少年抑郁这个主题有些兴趣,这与我有一定关系。说这句话并不是在说我是受害者,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有心理问题了,每隔一段时间都能在X上刷到吃盐自杀的推文,可这绝对不是因为他们心理脆弱,当很多人都无法呼吸的时候,这一定是空气出了问题,空气问题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 对空气安全的探索,把我引入了一个新的境地。
我之前从身心角度写过高考带给我们的伤害,我们将高考视作战争,使用战争来理解高考,于是我们得了战争后遗症。后面和ai聊这一视角时,祂为我提供了这一领域更加前沿的理论——将二元模型更新成了三元模型——多重迷走神经理论。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不仅仅是负责“战斗或逃跑”的交感神经系统,和负责“休息和消化”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在我们神经系统更深处,还有着一个不受我们意识控制的生存机制——负责冻结和假死的背侧迷走神经。
这一行为在很多动物上都有,当动物面临极端威胁时,动物并不会继续逃跑,而是直接冻结在原地,保持僵死状态,为身体节约最后的能量。我们人类这一动物的脑中也存在这一机制,在我们人类身上,这种僵死反应不止会发生在行为层面,表现为无法行动、僵在原地,也发生在心理层面,表现为“我被困住了”、解离、回避、麻木、极度绝望。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遭受到的威胁和压力也不只是来自物理层面,面临的并不是野兽袭击,而更多是心理、文化、社会层面的威胁。不过我们的神经系统仍然是几百万年前在非洲原始草原时的样子,我们的神经系统并不知道威胁来自野兽还是来自考试。于是我们的神经系统仍然在使用面对野兽的机制,来处理来自心理、文化、社会层面的威胁。
当我们遇到致命威胁时,我们的神经系统认为面对这一威胁,我们没有办法逃掉(if 没有威胁->放松,else if 威胁不大->战斗,else if 威胁较大->逃跑,else 僵死),于是选择激活了背侧迷走神经。身体进入冻结模式,主动将自我与身体感受分离,以一种旁观者视角等待野兽杀死我们,这一视角有助于减少痛苦。但是对我们人类来说,这一威胁居然不会生效,不会真正杀死我们。我们的神经系统并不知道这一点,在野兽离开后,仍然等待着死亡来临,身体不会从背侧迷走神经主导的冻结状态恢复。
也许这叫作创伤反应?好吧,我对创伤也已经祛魅了,创伤这个说法意味着需要被治愈,但这不过是身体在面对威胁时的适应策略,这在当时是有效的。一个在校园中遭受霸凌或其他什么伤害的孩子,在无法摆脱校园环境时,选择分离自我与感受,保持解离、麻木、回避状态,这有助于他适应环境。只是当环境改变之后,这种适应状态也需要得到有效调整。
一个健康个体的神经系统需要能够在面对压力时进入“战或逃”模式,在威胁消失之后,回到腹侧迷走神经主导的“休息和消化”模式,根本就不会进入冻结和僵死状态。
在对身心关系、放松、神经科学的探索过程中,我逐渐开始怀疑之前相信的观察者视角。
神赐之物
在一次与ai的闲聊中,我再次向ai提出了“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一庸俗问题,并且要求ai给出一个我不可能想到的视角。ai抛出了一个震撼我的前沿理论——自创生,这一理论提供了一个基于系统科学的生命定义。这一理论将生命看作一个网络,这个网络由很多过程组成,这些过程的唯一目的是不断维持和生成这个网络自身。
对于一个细胞来说,这个细胞并不是为了向外生产蛋白质,生产ATP而存在,它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维持和生成其自身。与自创生相对应的概念叫做他创生,对于一个汽车工厂来说,这个汽车工厂的目的是生产汽车,向外部提供汽车,而不是生成组成汽车工厂的组件,不是维持汽车工厂本身。(汽车工厂也要维持其自身,但是维持自身是其手段)
这一理论与我脑海中原有的系统科学知识产生了共振,为我提供了一个新视角(高中时买过一本《系统思考》,买之前以为这个系统是周密、结构化的意思,结果是systems)其并非从外部视角定义了生命,而是从各个组件之间的运作,从系统的角度定义了生命。
生命是自我维持和自我生成的存在,其意义、价值并不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其自身。生命的“是”就是其“应该”。
回归
在理解这一原理之后,我开始好奇并继续向ai提问,既然生命是维持自身的存在,既然生命的唯一目的是维持自身,那为什么人还会自杀呢?是什么让他们不能维持自身呢?
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解释自创生理论,对于一个自创生系统来说,其唯一目的是维持和生成其自身存在,但是其必须要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才能实现这一点。这一向外的交换动作发生在系统边界上,对于细胞来说,这一边界就是细胞膜,细胞通过这一膜结构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来维持和生成其自身的组件。
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的边界不只是身体的边界,也包括心灵的边界。边界并不是一道隔绝内外的墙,可以用防火墙或者半透膜来理解这里边界,我们需要能够控制我们想要的事物进入系统内部,也需要能够排出我们的代谢产物。外界的叙事通过伪装成能够通过认知防火墙的数据包,伪装成我们需要的养分,渗透进我们的系统。(我们的防火墙上充满着进化积累下来的漏洞)
我们需要什么呢?从外部视角来看,我们有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连接的需求,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
这是马斯洛的需求模型,外界如何劫持这几点呢? 我们需要满足生理需求,于是外界为我们提供了能够满足我们生理需求的商品;我们需要满足安全需求,于是有了国家、军队、法律、工资、保险的庇护;我们需要满足归属感,于是我们被赋予了不同的身份标签;我们需要满足尊重需求,于是有了财富、成绩、头衔、地位来量化我们的成就;我们需要自我实现,于是我们需要成为“成功人士”。
这些外部方案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们劫持了我们更底层的内部需求,从内部视角来看,我们需要拥有自主性——能够决定什么能够进出我们的系统,否则我们没法建立起自创生秩序(想象细胞膜破裂),我们需要拥有胜任感(成就感)——我们能够稳定产出用于维持我们系统的事物,我们需要拥有归属感——我们能够与环境中的其他个体进行协助,这能够提高我们维持自身的几率。
这三点是自我决定理论为我们揭示出来的核心内在需求,外界如何扭曲这三点呢?你拥有自主性,你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任何商品;你必须产出成果(分数、KPI、奖项、头衔、金钱),否则你就是失败的,你就没法有效维持自身系统稳定;你必须完全认同我们,不然你就是叛徒,你就会被抛弃,你就没法通过与环境中的其他个体进行有效互动,来获得支持。
外界系统为什么要扭曲我们的需求呢? 因为外界系统需要满足他们自我维持和生成的需求——国家、宗教、公司这些都可以看作自创生系统。国家需要通过法律、教育、意识形态、军队等体系来不断制造“公民”,然后公民又用于维持和生成法律、教育、意识形态等体系;宗教通过教义、仪式等来制造信徒,再通过信徒的实践来维持和生成教义和仪式;公司通过产品、企业文化、培训来制造员工,员工再通过与市场交互来维持和生成公司。
对于这些外界的自创生系统来说,我们是他们自我维持所需的原料。
你必须要服从系统的规则,你才拥有自由;你必须要为系统产出你才有价值,你必须认同系统内部的身份标签你才有归属感。
我们能够做什么呢?顺从或是利用系统运作逻辑,作为系统运作组件的同时实现自身的需求?但是系统会持续扭曲你的需求,你的需求并不等于系统的需求;反抗?这显得有些无力。因为系统不只是通过叙事来扭曲你的需求,还通过权力来取消对你的支持。企业能够解雇你,让你失去稳定的经济来源;宗教可以驱逐你,让你失去庇护和社群;国家可以取消你的身份证明,让你不再合法。这些取消会让我们无法满足我们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逃呢?我们能够逃到哪里呢?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宗教到另一个宗教,从一个企业到另外一个企业。只要我们不远离人群,逃进原始森林,那我们总会生活在某一个系统。
除了上述三种方式呢?这里我又得拿出悬置了。我们可以做个观察者,做一个玩第三人称游戏的玩家。理解系统运作逻辑,参与系统运作,但是并不认同那就是全部的现实。
最后的门槛
在正文最后一节,我只能够展示一些我看见的可能。这是本次冒险最后的门槛,从深渊回到日常,从认知上的理解到存在的状态。
回到最初那个愚蠢的问题吧,“饿了应该吃饭吗?”这个问题一度让我想过放弃记录本次冒险,但是我的确是被这个问题所召唤,才有了这场冒险。
这里的“应该”出自一个身心分离的视角,我是机器中的幽灵,我在控制我这具身体,我的身体向我传递了饥饿信号,我需要对此做出响应。
这叫作身心二元论,这来自笛卡尔。他尝试对一切事物保持怀疑,然后找到了一个无法被怀疑的对象,就是他说的“我思故我在”,然后以此为起点建立了他的身心二元论哲学体系,开启了西方近代哲学。在如今,这种二元论已经成为了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并且我们的日常语言、影视作品、小说以及宗教都在强化这一观念。
但是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前沿科学领域,这一视角已经被淘汰了,现在的最新版本——我们人类关于身心关系的最新认识——是具身认知。我们的心灵并不独立于身体存在,我们并不是机器中的幽灵,我们就是我们的肉身。我饿了,我就是那个感受着饥饿的活生生的肉体。
在召唤阶段的我,带有一种强烈的身心二分视角,所以我才会使用“应该”来发问,但实际上是“想要”。并且这里更加有趣的是,“我饿了,但是我不想要吃饭”。我居然被异化到如此地步,与身体分离的程度如此之深,我居然在外界叙事的扭曲下将来自本能的“想要”给抑制了,我居然忘记了我真正的需求。
我最终找到的道路是一条整合身心的道路,从身心二元到具身认知。 怎么实现这一更新呢?需要用身体来做到这一点,用行动来思考。在这条道路上,我看见了道教、佛教中的身体练习,看见了西方的费登奎斯方式,看见了苦行、朝圣等宗教仪式……
l1uyun
如果你读到了这里,那我相信你一定读到了这里。正如结构所暗示的,你刚刚读完的这些内容,是一个故事,一个我为了整合我自己混乱的思考,而建构出来的故事。这一故事并不是事实的回放,实际上的探索过程非线性并且充满噪声。
为了从充满噪声的数据中提取更多信息,我选择了使用一个结构来叙事。当然,我并不是先找到一个结构才开始写,而是先自由书写了一份草稿,然后在阅读草稿过程中涌现出了这个结构。
在涌现这个结构后,我将草稿分类填充进去,扩写成了这篇文章,最后还决定在当前这个位置描述我的写作行为本身。正文最后两章因为在草稿阶段只写下了几个关键词,以至于“回归”章节偏离了我的预期以及“最后的门槛”章节烂尾了。
我只是准备谈到如何区分需求和规训,并没有准备谈论叙事和权力,我还不足以写这些内容。在最后一章我想要介绍具身认知、费登奎斯方法以及宗教方法,准备在这里区分两种观察者,身心解离与身心合一的观察者。前者是特定环境下的适应策略,后者具有适应环境的能力。但是在写的时候还是回到了最开始的问题。
我的祛魅行为只是在换版本,从古老版本更新到前沿版本,背后是对科学的信仰。自创生只是我个人体系的第一性原理或者说只是个止痛剂,并不足以成为生命意义的第一性原理。这里面仍然发生了事实和价值的跳跃,我用科学概念重构了生命定义,用身体现象学消融了事实和价值的界限,将价值内嵌进了事实。
叙事不仅是外界系统扭曲我们的方式,我们自身也是通过讲故事来组织我们的生活,来从虚无中建构意义。我们可以接受一套现有的叙事,成为某个现有系统的成员,我们也可以选择成为讲故事的人,创造自己的个人叙事,并且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