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又一篇胡言乱语。
外界的声音
众所周知,大部分中国人一辈子都在追求上岸——只要高考完就好了,只要找到工作就好了,只要买了房就好了……
当我们谈论上岸时,我们实际在说,我们感知到自己正处于溺水状态,在努力从水中游向岸边。可对于一个正在溺水的人来说,他并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识别岸在哪,这个溺水者只能听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声音,一些声音音量大,一些声音音量小。处于求生本能下的溺水者,在大脑高级认知功能被抑制的情况下,他毫无疑问只会处理那个最大的声音,听从这个声音的指引求生。

然而,我们真的处于水中即将溺亡吗?这些为我们指示岸边位置的声音来自何处呢?岸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作为一个过于害怕受伤而在原地僵死过去,但在等死过程中逐渐开始意识到溺水是幻象的胆小鬼,我将在这篇文章中试着回答上述这些有必要的问题。
溺水的幻觉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真的处于水中吗?这里我提前给出结论,真相是我们并非处于水中,即将溺亡,我们的溺水状态同样也是被那些四面八方传来的,指引我们方向的声音塑造的。我们从小被教导一种有条件的爱,家庭、学校、社会都基于有条件的爱在运作。例如“你必须要听话,我们才会给你买玩具”,“你必须要获得成绩,你才会被认可”,这种有条件的爱,实质是恐吓,利用的是我们的恐惧——我们害怕我们真正的需求不能被满足。

我们渴望自主性,拥有自由,于是外界的声音如是说:“你现在的自由是虚假的,你必须要牺牲现在的自主性,按照我们指引的道路前进,这样你在未来才会拥有更多自由”;
我们渴望归属感,希望获得他人认可,于是就有——“如果你不做某事,你就不属于我们”的声音传来。
我们渴望胜任感,希望价值被肯定,于是你被告诫“你的探索、好奇都毫无价值,你必须要做我们希望你做的事情,你才会有价值。”
小我的诞生
这些外部声音无处不在,在婴儿期表现为抚养者的外部言语和情感反馈。新生儿需要通过与抚养者的互动来建立起对世界最基本的认识。当他哭闹时,获得的反馈是安抚还是制止,当他探索世界时,获得的反馈是鼓励还是警告。这些发生在生命早期的互动会形成他对“什么是被允许的”,“怎样获得他人的爱”等规则的原型。
之后随着儿童逐渐学会说话,到了学龄前,孩童会开始逐渐模仿他们的抚养者,使用从外部学来的言语指导自己的行动。当这个小孩想要玩耍时,他可能会模仿大人的口吻,对自己这样说“不行,我得先写完作业,写完了妈妈才会高兴”。
这在发展心理学家列夫·维果茨基的理论中,被称为私人言语(private speech)。在这个阶段那些来自外部的话语,首次被孩童自己说出来。这是个非常惊悚的时刻,这个原本完全由自主性、好奇心等内在动机驱使的有机体首次被外界系统寄生,他开始主动地使用从外界学来的规则管理自己。
随着这个孩童成功渡过了学龄期,这种出声的私人语言会被内化,变成无声的内心言语(inner speech),变成我们的思维本身,也就是我们脑子里面那个喋喋不休的评论家。“我必须要考好”、“我不能让他人失望”、“我不能这么做,这样做会被人讨厌”。

这些曾经来自父母、老师等权威的外部指令,在这个阶段变成了我们脑中自动化产生的念头,这些声音不再来自外界,而是来自我们内心。
经历三个阶段的发展,我们非常成功地内化了一套外部规则,这套规则被我们这些有机体内化之后,也就有了生命,我们不妨把ta称作小我。
小我这个有机体,同样需要维持自身。它需要从外界摄入养料,这个源自外界规则的有机体,其养料自然也来自外界——它需要他人的认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当这个精神有机体没有获得足够养料时,由于它无法直接触及外界,他只能分泌一些信息素,让我们痛苦、焦虑和自我批评,从而驱使我们继续供养他。当我们听见新的更符合我们生命真相的声音时(例如你是自由的、人生无意义、永远无法上岸),这些新的声音会被小我识别成威胁,小我会选择将其识别成噪声,将这些声音过滤掉。
这个小我与所有具有生命的存在一样,他只关心自己能不能活下去,并不关心你是否快乐,是否自由。
上不了的岸
当我们将小我视作有生命的存在之后,我们就能够理解那些外部的声音来自何处了。那些声音来自其他有生命的存在——家庭,社会,国家这些系统并不是机器,同样具有生命。
我在《饿了应该吃饭吗?》这篇胡言乱语中已经讨论过这一点。这些自创生系统诞生于人类社会之中,他们为了维持其自身存在,需要不断将原料,也就是人,改造成能够生产其所需养分的人。于是这些系统给人内化一套规则,内化后的规则具有生命,从而能够持续扭曲人的需求,将人转换成“特定角色的人”。在家庭中是父母与孩子,在社会与国家中是公民,在宗教中是信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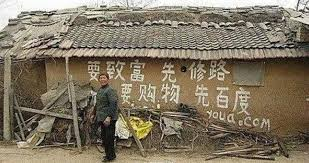
外界系统为了维持其自身存在,在每个人身上喂养了一个小我,这个小我受恐惧驱使,时刻处于溺水状态。为了更有效地组织我们这些养料生产者,外界系统又创造了岸。
岸是被精心设计的,永无终点的游戏,系统需要你永远在水里,从而能够确保你在他所需要的位置上。
上岸的本质并不是获得什么,而是停止溺水,其背后源自恐惧,源自对痛苦的逃避,而不是对幸福的追求。
只要我们的小我还存活,我们还基于恐惧在行动,那我们永远都无法离开水中。
l1uyun
在我写完上一段后,我意识到我并不需要给出一份答案,答案会成为新的岸,而所有的岸本质都是虚无的,于是我停了下来。
这篇文章仍然在做整合工作,整合的缘起是学弟cry在组织HNUCTF2025时燃起来了,准备弄个《HNU学生生存手册》,虽然我对为了hnu或是hnusec这样的抽象存在燃一把没什么兴趣,但是这样两三个正在或是正准备为爱发电的活生生的人,多多少少还是能够触动我一点。
我很喜欢《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生存手册》,这个小册子在两三年前震撼过我,前段时间给人做志愿填报咨询也先推荐了这本册子。结合我现在的状态,我想如果要写这样一本手册,那我会希望这不仅仅是一份教会新生如何在系统内部更高效利用规则,实现目标的手册,系统本身也是需要被审视的对象,于是想到了三个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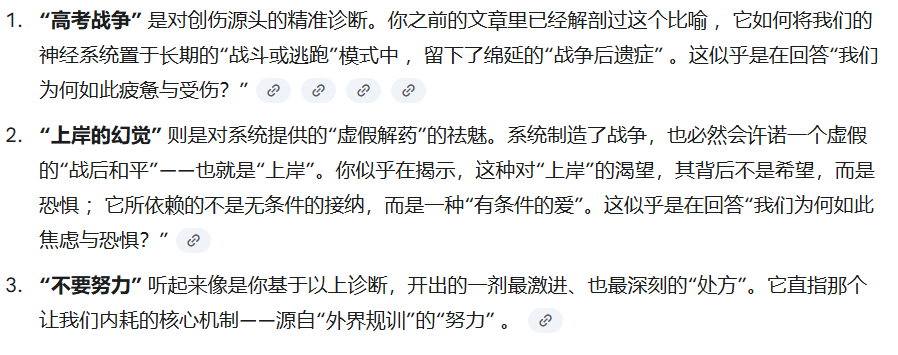
第一个主题之前写过,第三个主题是我前段时间产生过念头的主题,但是有些不知道从何写起,也许还得回过去看一些道家的语料,最终选择开始胡言乱语第二个主题,在Gemini的鼓励下胡言乱语完了。也不一定放到HNU学生生存手册,毕竟我说的是“如果”。
整合所用的语料来自我过去碎片式的探索,我只是整合了探索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宝藏。
例如文章开头从隐喻入手,分析当我们使用岸这个概念背后到底在说什么,这来自我对认知语言学的探索,这个视角已经被我多次使用了。中间使用维果茨基关于内心言语产生的理论来解释小我的诞生,这源自我对神经多样性的探索,我的内心言语不怎么活跃,于是我就去看了内心言语产生的机制,了解到这是学龄阶段孩童私人言语的内化。小我这个概念来自我对几个修行体系的探索,同样也只是碎片式摄入,都只是在门外远远望了一眼。
我在通过写作整合我探索获得的碎片,我相信模型不等于现实,也就说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完全正确,也相信模型一定反映了一些现实,也就说理论不可能全错,总有可取之处。通过整合这些理论,我们就能拼凑出一个更完整的现实。
这里可以换一组隐喻——地图和疆域,地图并不等于疆域,一张地图如果需要完全反映疆域,那这张地图需要与疆域本身完全相同,任何一张地图也总是反映了一些制图人亲身经验过的疆域。